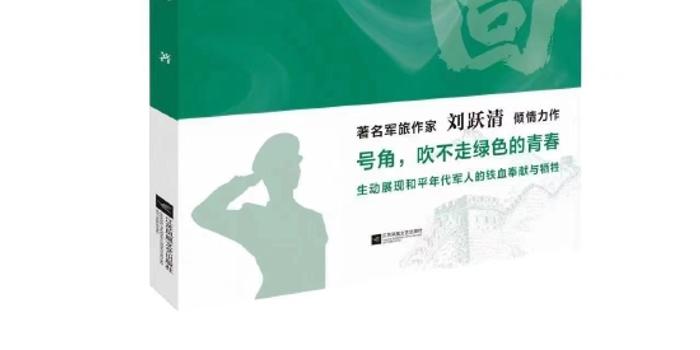鸽哨翩然八月的天空——读长篇军事小说《梦回吹角连营》

新浪江苏
关注刘跃清是一个让人尊重与敬佩的军人、作家,举手投足间和行云流水的文字一样,都带着磅礴大气和铁汉柔情。他1990年3月湖南隆回入伍来到驻南京东郊的光荣的“临汾旅”,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到2016年12月转业,26年的军旅生活,他心里应该积淀有很多的军营故事。
刘跃清的作品形象互补,尽见真淳的环境、故事情节和心理描写,彰显了他对于军事题材创作游刃有余的把控能力。他的人生阅历和军营经验都紧贴着当下的社会和军营,笔下多以描绘部队的现实生活见长。无论是描绘烽火连天的沙场鏖战,还是再现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刘跃清毫无例外都是将军人和军属作为描写对象,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军人的戎马生涯和日常生活。可以说,只要打开刘跃清的作品,就会有鲜明的兵味和斗志扑面而来,挥之不去。
近日,继长篇现实军事题材小说《士兵凶猛》、中篇小说集《连队之河》和长篇纪实文学《上甘岭43昼夜》《战斗在朝鲜》《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纪实》之后,刘跃清推出了最新军旅力作《梦回吹角连营》。为了写好这部小说,刘跃清历经几年,苦心创作。该书堪称以曳光弹般的笔触描述一群青春蓬勃的官兵,恣意汪洋地唱响军营青春行板。
我跟随着这些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听着刘跃清娓娓道来,走进了21世纪的军营。毕业于某地方名牌大学的李肇强、地方高中毕业考上军校的刘大勇和当了三年兵考军校靠走“曲线”来实现自我价值的老兵“我”,三人在新干部培训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配时,李肇强和我留在本岛直属保障分队,刘大勇被分在远离本岛的小岛,此后虽难得一见却惺惺相惜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忠职守,发生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故事。
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以“鲜花盛开的世界”、“云中谁寄锦书来”、“碧海蓝天夜夜心”、“莫愁前路无知己”和“永不消失的番号”为题,缓缓拉开了吹角连营的大幕。以我为第一视角,主线通过李肇强、刘大勇和我(刘小虎)的成长经历,副线通过江流影、张巧云、李晓琳等人物故事的穿插并行,以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新时代军人、军属和干部的群体风采。这里有抗震救灾的生死直面,有军中爱情的刻骨铭心,有真枪实弹的沙场训练,有战友亲朋的深情厚谊,也有部队军改的猎猎号角。这部著作将军人意识、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等体现的淋漓尽致,满足了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心中空虚失落的精神需求,发挥了军旅文学的特殊使命和对读者的积极启发与影响。
地震、洪灾、救援现场这些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特殊事件,由刘跃清通过环境、动作、语言、细节的细腻描写真实残酷地展现在了眼前。
一栋六层教学楼已夷为平地,砖石遍地,水泥板耸立。成百上千的家长或围着废墟,或翻扒瓦砾,或攀爬在残垣断壁间,呼唤,寻找。每一声喊都牵肠挂肚,每一张脸都泪雨滂沱。“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解放军快救孩子们吧。”拉上警戒绳,家长们不用劝说,立即离开废墟。
我们带着钢钎、铁锹等简易工具冲进废墟,迅速行动起来,有工具的奋力挖,没有工具的就用双手刨。第一个孩子救出来了,家长紧紧搂住孩子,长跪不起。一个接一个孩子救出来,家长抱住送孩子的兵,泪流满面,语无伦次地说着感激的话。
群山如疮,满目废墟。热浪一股一股地掀过来,夹杂着浸入肌肤、刺入骨髓、绕不开、洗不掉令人做呕的恶臭。
地震,与死神赛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与自己赛跑。
江流影翻过一块巨石时,腰一闪,几乎跌倒。平时还算合身的迷彩服这时套在他身上就像用根竹竿挑着,湿漉漉的,背上的“盐碱地”又一次被水淹没。
一群绿头苍蝇趴在浮土碎石上,我一锹挥过去,轰地一声散开,很快又飞了回来。这下面有人,而且埋得不深。我小心翼翼地从周边开始刨起。江流影考古似的,一点一点地扒,像是怕惊醒下面沉睡的人。很快挖到一层浇过油一样的湿土,遗体清理出来了,是个老年男性。我把裹尸袋摊好,打开。江流影眼睑低垂,铁锹始终机械的在遗体周边扒来扒去。“搭个手!”将遗体搬进裹尸袋需两个人抬。江流影犹犹豫豫地伸出右手,塑胶手套戴在上面,僵得像根木棒,那样子好像是让老人抓住,叫他自己爬出来。我一咳嗽。江流影浑身一抖,抓起一只紫色胀肿得吹了气一样的手,刚一碰,那只手像在火上炖过很长时间,烂肉尸水扑扑往下落……他抓起骷髅手用力一拉,没想到整支胳膊竟从腋窝处脱落。江流影一屁股坐在地上,终于看了一眼坑里的遗体,遗体突兀的眼球有绿水正缓缓流出……啊!江流影被火灼烫一样将手里的胳膊扔出,蹲在地上哇哇大吐。直到我把遗体一点点挪进裹尸袋,收拾停当,他还在吐,吐的都是胆水,没有星点食物。我们都有几天没吃东西了,吃什么吐什么。
江流影身子一躬,退了出来,怀里紧紧搂着个孩子。他转身刚跑,轰地一声,危墙倒塌,雨中腾起几缕细淡的灰尘,将窄小的洞口堵得严严实实。我冲向前接过孩子,小小卷缩的身躯冰凉冰凉的,还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看着我们。
“狗日的地震,我操你娘!”我仰头大喊,发疯一样。
江流影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就那么怔怔地站着,一动不动,任凭雨在他身上浇,风在他身上抽……后来,江流影对我说,排长,你也是条狗。狗日的地震,你操它娘,所以你是一条狗。说这话时,他已经病了。
这些段落细节的描写中有救死扶伤带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也有直面男女老幼遇难者的遗体回天无力时带来的失败感和绝望感,我们深切体会到了战士们身体、心灵承受的伤痛远比平常人经历的更多更沉重。刘跃清拿起电影镜头的取景器,运用近景推进、远景切换和人物特写的手法将这些血淋淋的视觉体验和生命冲击植入读者的脑海引发共鸣,为新兵战士江流影受到心理创伤应激反应和发生意外做了翔实的铺垫,也借此表达对于军人心理创伤及时开展专业辅导的大力呼吁。
军营里的爱情带着别样的纯粹、朦胧和美好期待,刘跃清用或婉转浪漫或刚强悲壮的笔触将李肇强对张巧云的默默追求和李肇强牺牲后连队里不变的仪式一一展现,赞美了特有的军营爱情和军人深情。
李肇强给张巧云的信每次都没有封口,有一次我在路边悄悄打开看了一眼,就看到一句话:在所有的药物中你的笑容是最好的一剂。
李肇强牺牲后,我们连队像其他连队对待牺牲了的英雄一样,晚点名时,第一个点英雄的名字,全连官兵吼着喉咙答到。同时,保留英雄的铺位,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单一尘不染。指导员说,这是让我们感受英雄的气息,在崇尚英雄的环境中成长。
“云雾满山飘 海水绕海礁 人都说咱岛儿小 远离大陆在前哨”,刘跃清在舟山群岛的东极岛上听着《战士的第二故乡》的动人旋律,将充满独特的海岛浪漫和战友深情自然流淌于纸上。
在刘大勇的眼里、话里,小岛只有夏天,春天、秋天和冬天都隐退在大海深处。而爱人李晓琳在漫长的两地分居季节里只领略过小岛的冬天。
十八九岁,青春躁动的年纪被从故土连根拔起,移植小岛上,风雨中站立成一盏航灯,一盘礁石,支撑的只是纪律和信念。
听刘大勇说,每当有兵休假,离队前连队干部找谈话的最后一句就是嘱咐,回来时别忘了带一包家乡的种子,菜种或花种都行。顺便带一包土,怕种子娇贵,水土不服,种的时候把“老娘土”和岛上的土掺在一起。这个传统已延续多年。
刘跃清的文字功候深藏,细腻内涵,对于军人和军嫂的内心独白和心理描写相当生动,对于战士们爱岛如家的坚定信念描写也是细致入微。
很多这样的地方,在怡情的人们眼里它是景点,到此一游;在士兵眼里它是阵地,需风雨守望。就像有的海滨浴场,一边是晒得黑乎乎、皮开肉绽的士兵,一边是红男绿女、欢歌燕舞。战争与和平就在一起,并肩行走。
刘跃清还非常擅长对照比较的手法,将事物、现象和过程中的矛盾双方,在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形成相辅相成的比照和呼应关系。这种手法充分显示了所有的岁月静好背后,都有军人的负重前行,加强了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而在海岛之上,中士一班长和刘大勇等雷达哨所几个兵早已练就“看波形辩船只,听声音知船型,见大小判距离”的“屠龙之技”。在处理外国军舰突然靠近领海的事件中,战士们的快速应对反映了守岛战士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以及国防意识的大局观和勇敢担当。一枚不炸弹夺去了刘大勇的生命,他在爆炸现场毫不迟疑地将战友张胜才保护在身下的反应,更是一种危机的体认和军人刻入骨髓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
军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也是军事文学的重要素材来源,军人从来不是生活在真空状态中的,他们与社会现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人为本的精神落实到每位军人身上时代涌动的产物。过去面对的更多的是战场硝烟,如今的军营现实更多的困扰是食堂、军人服务社、军需处、纠察队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以及军改和干部选拔带来的紧张斗争,因而关注每个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是和平时期军营中最受关注的现象。
刘跃清将转业干部的不同需求和心理描摹得淋漓尽致,将“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言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的徐缓苍凉和悲壮忧伤演绎的透彻酣畅,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洗尽铅华真纯毕现,作者的良知和勇气也是可圈可点。
掩卷长思,感人肺腑。刘跃清用丰富的人生阅历、深挚的军营情感积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淳朴深情的文字,构成了一组现代版的“从军行”。他让我们看到了几个年轻生命的猝然牺牲,也看到了一代代军人和军属背后的默默付出,让我们的心灵世界受到巨大冲击,涌动起对个人、家事、军事和国事的深切关注和厚重震撼。这是超越自我的锐意创新,是极致走心的深度创作,也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再次洗礼。
在灾难、病痛和战争面前,我们人类是如此地渺小,命运是如此的无常,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来临。军人用血肉浇筑成保护我们的钢铁长城,我们所处的和平时代是何等来之不易,应该更加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我想一部好作品的文学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卢云)